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合法性的行政与司法判定标准
——解读最高人民法院驳回海南裕泰公司再审裁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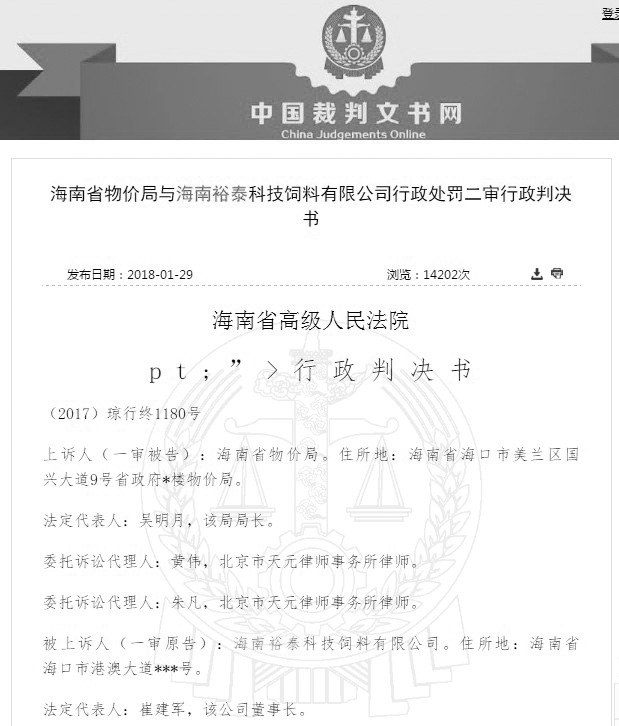
在我国,对纵向垄断协议尤其是转售价格维持行为(RPM)合法与否的判定,长期以来一直是令企业感到困惑的一大难题,重要原因在于行政与司法对RPM是否构成本身违法判断标准不统一。相应的,反垄断理论研究与实务界也划分为两大阵营,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分别支持企业的RPM行为应适用本身违法以及需进行合理性分析两大派别。
《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查处了较多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2019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某汽车公司的固定或限制最低转售价格(RPM)行为。2017年,上海查处了伊士曼品牌航空涡轮润滑油、捷波朗品牌耳机RPM案,江苏查处了江苏百胜电子有限公司(VIVO手机江苏总经销)RPM案。以上案件,从总局到地方执法机关在对RPM的行政处罚决定中,采取的均是本身违法认定方法,即依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直接推定行为的违法性。这些案件的查处,有效震慑了实施相关违法行为的企业。
然而,司法机关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的合法性判定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举证责任与认定方法。在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案、东莞横沥国昌电器商店诉东莞市晟世欣兴格力贸易有限公司案中,上海与广东地区法院均采取了合理原则。法院认为,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必须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才能被认定为垄断协议。《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同样限定该法第十四条的纵向协议行为。同时,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举证责任在于原告,原告承担举证不利的后果。仅证明被告采取了转售价格维持行为,并不足以认定其行为的违法性。这些案件的裁判结果体现了司法与行政执法标准的不同,但此前两者尚未在个案中直接发生冲突。
案情回顾
海南裕泰公司垄断案则将这种差异带来的判定冲突直接摆上台面。作为我国第一起纵向垄断协议的行政诉讼案件,海南裕泰垄断案历经一审、二审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裁定,三个层级法院的判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该案由此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裁决在一定时期内对纵向垄断协议的执法与司法将具有极大的参考和指引价值。
本案中,原海南省物价局于2017年2月28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海南裕泰公司与经销商签订的《饲料产品销售合同》第七条,即要求经销商对让利标准保密并服从甲方的销售指导价,违反了《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一项“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价格”的法律规定,由于经销商并未实施该垄断协议且海南裕泰公司在调查中积极配合,最终被处以20万元的罚款。随后,海南裕泰公司不服此行政处罚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需结合该法十三条第二款综合考虑相关价格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也就是说,仅仅形式满足该法十四条的纵向协议形式要件,并不意味着这就是一个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证明协议对竞争的排除和限制效果。一审认为海南裕泰公司的经营规模和市场份额等因素决定其合同规定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不构成垄断协议。判决原海南省物价局撤销其行政处罚决定。原海南省物价局不服,提起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垄断行为规制的原因在于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对垄断行为不仅要制止,还要预防。《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的固定转售价格协议并不以该法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排除、限制竞争”为构成要件。因此,只有经营者提交证据证明其协议满足该法十五条的适用除外情形,才可免除处罚。法院同时认为,民事诉讼中涉及垄断行为的民事案件以造成实际损失为前提,而产生实际损失必然以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前提,因此与行政诉讼的证明要求存在差异。二审判决首次提出民事与行政案件中纵向垄断协议证明与判定的标准。
二审判决生效后,原告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最高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8日作出裁定,驳回原告的申请。
裁判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明晰了本案的争议焦点为海南裕泰公司与经销商之间签订的限制价格协议是否构成纵向垄断协议,并围绕该焦点进行说理阐述。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中的几个核心要点,对未来企业开展合规、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强执法和司法机关提升裁判效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未认定固定转售价格及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本身违法,认为其属于较为典型的纵向垄断协议,往往具有限制竞争和促进竞争的双面效应。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转售价格维持的违法性判定采取的是大概率判断,意味着本质上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认为RPM应适用合理原则。
二是最高人民法院纠正了二审法院的做法,明确认为《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对垄断协议应是排除、限制竞争之限定原则也适用于该法第十四条。《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究竟只限定该法第十三条横向协议行为,还是对垄断协议整体构成概括性限定,引发大量争论。此前二审法院从语义逻辑学上认为,《反垄断法》直接将“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视为垄断协议并明令禁止,该法第十四条规定的达成固定转售价格之垄断协议并不以该法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为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中明确此观点为错误,认定判断纵向垄断协议的构成仍然以排除、限制竞争为要件。
三是在行政执法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只需认定经营者从事相关行为,不必存在证明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即可认定构成纵向垄断协议。若按前述第二点,似乎行政机关不能证实存在纵向协议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就不能认定纵向价格限制行为构成垄断行为。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应用了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法律适用的社会现实状况分析,最终得出结论:反垄断执法机构一经调查经营者存在转售价格限制或固定价格行为,即可认定垄断协议,只能由被调查经营者通过提交满足《反垄断法》第十五条的证据进行抗辩。其依据为:基于当前的市场体制环境和反垄断执法实际,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对纵向垄断协议全部进行全面调查和复杂的经济分析,以确定其对竞争秩序的影响,将极大增加执法成本,降低执法效率,不能满足当前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需要。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经过调查证实经营者存在上述两种情况,即可认定为垄断协议,无须对该协议是否符合“排除、限制竞争”这一构成要件承担举证责任。除非经营者通过提交证据进行抗辩予以推翻。这一阐述保障了既往RPM行政执法案件的有效性,使得未来反垄断执法机构仍能够按照既往方式查处RPM案件,对企业的纵向合规行为有明确指引效果。
四是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法院需要审查垄断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判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原告诉讼请求得到支持的前提即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经营者实施反垄断行为给原告造成损失。而给原告造成损失是垄断行为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直接体现。垄断协议不仅要达成而且要实施并产生损失,此时的垄断协议当然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因此,在反垄断民事诉讼中,法院审查垄断协议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判定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前行政与司法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差异化认知给出了解决之道,但诸多疑问仍然只能等待全国人大修改《反垄断法》或相关部门出台解释、规章予以解决。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裁定的最后也建议反垄断执法机构总结执法经验,及时出台有关纵向价格反垄断执法指南,进一步明确执法标准,给予经营者明确预期。相比反垄断执法机构拥有反垄断执法专业人员、法定调查手段,民事个体的证明责任不应高于行政执法才能体现责任分配合理性。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反垄断法》的修改能够正视这一现实问题,完善纵向垄断协议立法,破除争议,统一标准。
□暨南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副教授 仲 春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