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沂某商贸公司未经批准从事直销活动案解析
案情简介
2018年1月,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管局接到举报,称某直销企业下属团队K公司以直销业务为平台,以直销化妆品为名搞传销。接报后,扬州市市场监管局迅速立案并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协查,调取了该团队负责人林某及其他20余人名下所有银行卡流水,通过财务分析软件进行比对分析,理出林某所属团队涉嫌参与传销人员约1万多人。因本案案值较大,扬州市市场监管局经过研判认为林某的行为涉嫌构成组织领导传销罪,遂于2018年4月将该案件移交给公安机关。又因该案线索涉及K公司未经批准在扬州市从事直销经营活动,扬州市市场监管局与公安机关达成分别立案、分别调查共识。由公安机关对林某涉嫌组织领导传销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对K公司违规直销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初查情况
扬州市市场监管局调查人员通过举报人提供QQ电子数据文档分析,确定当事人林某从属的营销团队名称为飞翔团队,林某系该团队的核心层人员。从业务运行轨迹看,飞翔团队与K公司属于两个组织,在直销活动中两者属于合作关系。飞翔团队自行设计了直销模式制度,以临沂某商贸公司作为法人登记组织与K公司发生业务往来。调查人员通过第三方平台的数据及双方财务往来查实,飞翔团队的直销模式是:将发展会员交纳的货款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归集于临沂某商贸公司。而后临沂某商贸公司向K公司提出订货需求,K公司按临沂某商贸公司需求发货,并提供货款的增值税发票。临沂某商贸公司按发票数额将货款汇给K公司。双方每一笔购货往来对应很清楚,属于传统的贸易关系。飞翔团队会员业绩的返利亦由临沂某商贸公司通过在第三方支付平台开设的户头支付,与K公司没有关联。这个初步调查结果与调查人员原先设想的K公司主导的违法直销活动有较大出入。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扬州市市场监管局重新立案,将违法主体由原先的K公司变为临沂某商贸公司。
处理结果
调查人员经一年多调查查明,2015年1月,临沂某商贸公司与K公司签订了经销商代理协议,双方约定K公司授权商贸公司以商贸公司名义专门销售K公司生产的系列化妆品。2015年3月,临沂某商贸公司在未经商务部门批准核发直销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直销员陈某发展会员,从事直销经营活动。2015年5月13日至2016年3月16日,临沂某商贸公司通过直销员陈某在扬州市发展了林某、王某、周某、毛某等会员300多人,直销收入计2315190元。鉴于临沂某商贸公司的行为违反了《直销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未经批准从事直销活动行为。2019年6月12日,扬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对临沂某商贸公司作出“没收违法直销销售收入2315190元、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
本案焦点
1.违法主体如何确定?
本案涉及的违法事实比较清楚,但如何确定违法主体相对比较复杂。当前直销市场直销主体的监管难度较大,一些挂靠直销企业团队、直销企业经销商、直销员及冠以“优惠顾客、会员”身份的自然人,各类主体身份相互交织,较难分辨。就本案来讲,主体身份涉及K公司、临沂某商贸公司、头目林某、直销员陈某等。要想确定谁是违法主体,需要执法人员从买卖关系、资金关联两个方面来确定。一是从法律关系上来讲,买卖关系是确定违法主体的主要标准,即从消费者(会员)角度来看,确定其跟谁买的产品,从而确定买卖双方;二是从资金关联方面来讲,资金流水归集是确定违法主体的重要标准,即消费者(会员)的款项最终归集到谁的账户名下。本案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取证固定事实,确定违法主体为临沂某商贸公司,符合基本事实。从上述分析可知,确定买卖关系、查清资金关联,对于直销案件违法主体认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传销案件移送后,能否立案调查违规直销?
直销企业的违规直销经营活动,往往与传销行为交织共生。而一旦查实传销行为,很多达到刑责标准。市场监管部门对于传销案件查办一般有两种处置方法:一是将案情线索及材料移交公安机关,市场监管部门不再办理;二是先行对传销案件进行查处终结,再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这两种处置方法各有不完美之处。不办理直接移交,案源流失,作为办案人员来讲有遗憾之处;先处罚后移交,存在随着时间后延犯罪嫌疑人有脱逃或者隐匿毁灭重要证据的可能,从而影响刑事追责导致渎职的后果。本案的查处给执法人员提供了第三条可选择的路径,即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合作,公安机关查处传销,市场监管部门查处违规直销,各司其职,分别处理。这个路径的可行性在于:一是从行为构成要件上来讲,直销和传销符合两个行为的构成要件,是两种行为,司法、行政分别处理不属于重复规制;二是违规直销涉及的具体表现较传销更为广泛,《直销管理条例》列举了14类违规直销行为,大多数与传销行为并无交织,因此也不存在一事两罚的问题。同时,这种分别处理的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好处:一是避免了对违法行为行政、司法重复处理合法性的争执;二是司法调查和行政调查的证据可以共享。本案中,扬州市市场监管局拿到的一些重要证据都来源于公安机关查实的证据,司法调查为行政调查提供了有力支撑。
案例评析
本案是扬州市市场监管局近年来处罚金额较大的违规直销案件,调查时间之长、组织人员之众、经费投入之多均创下了历史之最。本案的成功办结,体现了办案人员缜密的办案思路、先进的技术手段、钻研的工作作风。办案人员总结了三点经验:一是办案人员通过全国审判文书数据库获取了全国涉及K公司传销的司法判例6起,从中选择了外省某公安机关侦办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同类案件,掌握了有效的办案路径;二是执法人员通过网络监测技术手段进入了飞翔团队的服务器,并委托阿里公司云服务器协查固定了大量的经营信息证据,通过重庆市智信电子数据司法鉴定所进行证据保全,委托扬州专业网络服务机构对硬盘数据进行恢复;三是善于驾驭“大气候”,借助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的东风,整合各执法部门办案力量,同时加大普法宣传力度,让当事人主动投案协助调查。这些办案经验为今后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开展直销行业的监管以及查处传销、违规直销案件提供了参考。
办案启示
1.违规直销案件的查处难度加大,违法行为较难溯及直销公司。
目前,市场监管部门查办的直销违规案件,直销企业是违法主体的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案件查办中指向直销企业的证据较难获取,仅能收集到经销商、直销员的相关证据。本案当事人K公司的传销手法及上下线图,是其2015年5月之前的制度设计,之后K公司废弃了这种制度。调查人员查处的初衷原来指向K公司本身,但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资金链一直在会员与临沂某商贸公司之间循环,并没有归集到K公司。因而不能将K公司列为违法主体。这种现象说明,随着对直销违法行为查处力度不断加大,使得一些直销企业在企业与经销商之间构建一道防火墙,以往调查案件在证据上关注的指向直销企业的资金进出流水、给付报酬流水、电子积分结算、劳务发票、网络平台电子账户材料等,均无法在本案上得到复制。
2.调查手段受限,第三方支付平台取证配合度成了调查取证的关键。
由于近年来企业、个人特别是直销企业及所属团队广泛使用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往来结算、支付返利,让从资金链入手调查、确定违法行为与直销企业之间关联的查证方法面临挑战。一些直销企业及从属团队选择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流转资金,不仅是为了财务便捷,也是为了隐蔽灰色地带。直销业务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结算往来资金,只能反映财务的首尾两端,事实上屏蔽中断了财务的中间段信息,客观上造成了执法部门取证困难。从本案公安机关调查反馈的信息看,因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属于银行系统,故目前执法机关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监管处于半真空状态。一些规模较大的支付平台相对比较正规,数据存储管理比较规范,对执法机关的配合度也较高。但一些小规模的支付平台运行极不规范,对于公安机关及其他执法部门的查询,往往以业务访问量巨大为由久拖不办。本案资金结算涉及的A支付公司、B支付公司两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公司总部均在上海浦东。其中,A支付公司较为配合,满足了扬州市市场监管局提出的大部分查询需求,而B支付公司由于K公司及商贸公司大客户的身份,对扬州市市场监管局的查询需求拖延不办。本案的关键数据均在B支付公司,B支付公司的不配合给办案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较大困难。办案人员4次赴B支付公司取证,前三次均受阻,最后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才取得相关证据。
3.直销企业涉传行为较难定性。
本案的调查是两条线齐头并进,即刑事调查与行政调查同时开展,相互支持,证据共享。本案刑事调查对行政调查的深入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对传销的刑事定性难度很大,截至本案违法直销行政调查结案,刑事层面还未能进一步推进。需要注意的是,传销够不够刑责,不仅是团队计酬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要考察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危害性程度。这不仅是司法机关办理传销案件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江苏省扬州市市场监管局 叶 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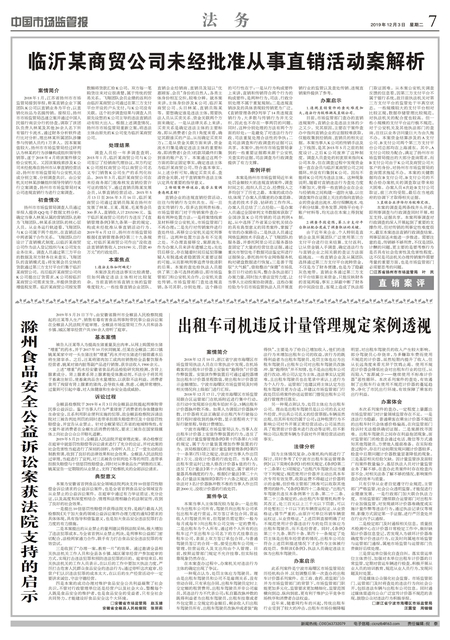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